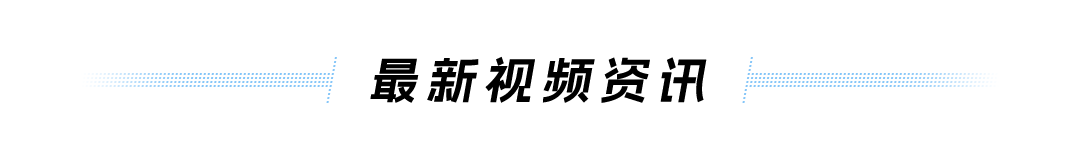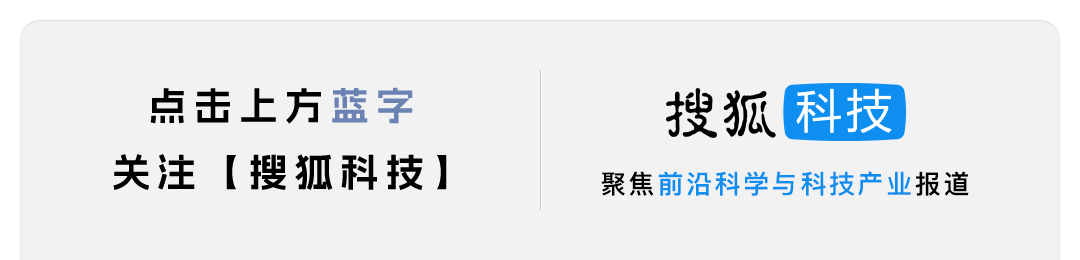

搜狐科技《思想大爆炸——对话科学家》栏目第121期,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副所长、李政道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丁洪。
嘉宾简介:
丁洪,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副所长、李政道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首任主席,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庆典Program Committee联席主席。

原始发现是不容易做的,第一次确实有运气成分在,后来慢慢摸索出了方法。
基础研究刚开始可能没有明显的作用,但之后会做的很好,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做科研挺辛苦,要enjoy life,没有体会人生之美,也没法追求科学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凝聚态物理,至少在实验方面不比美国差。
AI会增强创造力,以后AI看我们的智慧,可能就像我们看猫的智慧。
出品|搜狐科技
作者|周锦童
编辑|杨 锦
在基础物理的探索路上,总有一些名字与重大的突破紧密相连,丁洪便是其中之一。
他在固体材料中发现外尔费米子,推动“梦之线”“梦之环”“梦之城”等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深耕高温超导与拓扑量子计算领域,保持着十年一个重大成果的科研节奏。
谈及这些成果时,丁洪笑称:“原始发现是不容易做的,可能我的运气比较好,第一次确实有运气成分在,后来慢慢摸索出了方法。”
他还笑称自己“不务正业”,“我很喜欢跨界,做科研就是为了推动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进步,既然是这个目的,做规划也是很好的推动,有这样的参与机会我都是自告奋勇的。”
在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庆典上,搜狐科技对话了这位爱“跨界”的科学家,听他分享中国凝聚态物理的发展情况,当下“内卷”的科研现状以及AI加速科研进程的新可能。
“我们国家的凝聚态物理,至少在实验方面不比美国差。”丁洪对搜狐科技说道。
自从2008年丁洪回国以来,中国凝聚态物理发展非常迅速,这得益于政府的大量投入、家长对子女从事科学研究的支持,以及华人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优势。
虽然这可能有些“卷”的意味,但丁洪认为,“卷”是有积极意义的,竞争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有些“内卷”是无意义的消耗和资源浪费。
此外,他还表示,AI会增强创造力,在AI的帮助下,未来拓扑量子计算和高温超导领域会有巨大突破,预计20年内可能出现实用量子计算机,更高温度、更实用的超导体,核聚变也可能在20年内实现商业化应用,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
以下为对话实录(经整理编辑)
媒体:您能不能简单科普一下,外尔费米子到底是什么?
丁洪:费米子是一种自旋为半整数的基本粒子,例如电子、质子、中子等都是费米子。1928年狄拉克把狭义相对论引进了量子力学,外尔费米子是1929年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赫尔曼·外尔在狄拉克方程的基础上,预言一种无质量的具有相反“手性”的粒子。
宇宙中是否存在“外尔”基本粒子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我们非常有幸在2015年第一次在“固体宇宙”中发现了以准粒子形式存在的外尔费米子。
媒体:这在未来会有什么应用?
丁洪:带有“手性”的外尔费米子有可能做成低功耗的器件,有些很特殊的光电响应,所以大家都憧憬有很好的应用,但目前主要还是在做光电探测器,我们也非常期待以后有更多的应用。
媒体:您觉得未来基础物理会如何改变世界?
丁洪:基础物理一直在改变世界,未来也会如此。比如说发现电子的时候,有人觉得电子没有用,但现在电子变得非常有用,比如电子学、电子器件等等。
后来相对论解释高速运动的物质、解释宇宙、黑洞,可能和日常关系不太大,但是我们现在手机上用的GPS减小定位误差就需要考虑到相对论效应的影响。基础研究刚开始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作用,但之后往往会发现有很大的应用价值,所以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媒体:每10年您都会有一个重大的成果发现,是怎么做到的?
丁洪:我通常的回答是我运气比较好。原始的发现是不容易做的,第一次可能有一定运气成分在,后来是有方法的。
首先我们会去研究什么值得去做,研究课题挑选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步要知道什么是我们能做的,第三步就是怎么做。研究都在激烈的进展中,所以怎么样能有很强的执行力,能够率先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一套方法,形成一套经验。有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10年才有大成果,能不能更快一些,现在我们有AI的帮助,确实可以极大地加速。
媒体:您积极参与了“梦之线”“梦之环”“梦之城”三大科学工程的规划和建设,像科学城规化这种工作跟科研可能没有太多关系,您为什么会投入其中?
丁洪:我喜欢跨界,甚至有点“不务正业”。但反过来想,其实我们做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我们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进步,既然是这个目的,做科学规划也是种很好的推动,有这样的参与机会我往往是自告奋勇的。
媒体:您觉得这种大科学装置对基础物理的发展有什么推动作用?
丁洪:有非常大的作用。“梦之线”是指上海光源中的一条性能指标世界一流的光束线站,是由我们团队设计并建设的,建好之后我们就发现了外尔费米子。“梦之环”是指北京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世界上亮度最高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虽然我以前做的是低能的光电子研究,但现在马上建好了,我发现我也可以用,因为我们现在做拓扑量子器件,需要高能X光穿透。“梦之城”更多的是对整个科学起到作用。
科学城更是这样,我在美国待了18年,看到美国的一些成功的科学范式,像国家实验室和科学城,所以我2008年回国就投入到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事业中,规划和建设了一批大科学装置,还推动了一系列交叉研究平台。
媒体:您曾经说“没有科研的生活不可想象,但是人生也不可能只有科研”,科研对您意味着什么?科研之外您喜欢做什么?
丁洪:我是比较喜欢跨界的,喜欢做一些其他的事,除了做科研也喜欢做些规划,做些科普,还喜欢听听音乐。我前几天还成立了大理李政道科学艺术中心,邀请了多位科学家和艺术家进行了科学艺术之美的分享,大家觉得非常好。
其实有时候只做自己“一亩三分地”,事情做得比较窄,做些广的事情是比较好的,也能从中得到不少的启发,获得一些灵感。而且做科研是很辛苦的,也需要休息,需要enjoy life,没有体会人生之美,也没法追求科学的发展。
媒体:您觉得当前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有哪些问题和挑战?年轻人该如何面对学历贬值的困境?
丁洪:学历贬值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其实以前知识的获得是成本比较高的,为什么要去好大学,因为好大学有好的图书馆,可以看很多资料,后来有互联网之后这个壁垒就没有了,以后有AI的话,获得知识的壁垒就更少,人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
但是现在可能一些工作会被AI替代,比如编程,原来做“码农”很挣钱,但今后的做简单编程可能不行了,所以我们要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这就对人的知识要求更多了,当然AI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
我想最终到了足够发达情况,就会按需分配,让工作不只是一个谋生的手段,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媒体:您觉得AI会不会削弱创造力?
丁洪:我觉得AI会增强创造力,我认为地球的智慧正在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变。20万前是智慧从猿猴到人脑,现在是从人脑到AI,以后AI看我们的智慧,可能就像我们看猫的智慧。我相信AI达到一定高度之后,道德水准也会更高,对我们会更友善。
我现在也会让AI帮我看资料、写报告,我们研究很多的时间是花在做调研报告上,以前可能需要花两个月做调研报告,现在用AI可能两小时甚至两分钟就完成了。
媒体:高温超导机理是物理学界公认的难题,您认为当前最可能突破的研究路径是什么?
丁洪:我一直是研究高温超导的,高温超导现在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它的机理还不清楚,常规超导的机理在1957年就解决了,但1986年出现的高温超导就打破了这个常规理论,所以要发展新的理论,但现在过去了快40年也没有看到,到目前人们已经提出了上千种理论,到底哪个对还不好说。
第二大挑战就是高温超导体怎么很好地应用,高温超导体虽然具有高温、高抗磁性的特征,但是应用它往往需要跟普通金属一样具有有延展性,金属线可以加工,可以造成线圈,但高温超导体是陶瓷材料,绕线圈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怎样解决材料的问题也是个难题。现在高温超导在核聚变领域应用前景很好,像上海超导制成的高温超导带材就供不应求。
媒体:我国在凝聚态物理研究领域,对比国际领先水平处在怎样的位置?
丁洪:从我2008年回国到现在,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国的凝聚态物理有了飞速的发展,速度发展之快对于我们行业中人来说都感觉到很吃惊。我们国家的凝聚态物理,至少在实验方面不比美国差。
这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大量投入,中国家长对小孩从事科学的大力支持,不光是中国的科学家,连美国的很多科学家都是华人,我们华人具有很大的人才优势,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将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媒体:您觉不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一种内卷的现象?
丁洪:我们以前看觉得日本科学发展非常快,日本物理做得非常好,也获得了很多诺贝尔奖,但现在看日本新一代,感觉没有太多杰出的科学家。日本曾经也是很卷的,但现在躺平了,躺平的结果就是优秀科学家少了,所以“卷”有卷的积极的社会意义,竞争也能促进人类社会快速发展。
媒体:您曾说“做科研是一场马拉松,必须玩命的投入”,您是不是也“卷”自己?
丁洪:我显然不是一个非常“卷”的人。有些“内卷”是消耗的,是无意义的。比如挤地铁,发现车站很挤,反方向坐到终点得到位置,但大家都这么做,就毫无意义、浪费资源。
媒体:您觉得在凝聚态物理和量子材料领域,未来5-10年内会取得哪些重大的突破?
丁洪:我现在做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拓扑量子计算,另一方面是高温超导,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未来这两方面都会有巨大的突破,未来20年可能会有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出现。第二个就是会有更高温度、更实用的超导体出现。核聚变在未来20年内也有可能做到商业化,带来一些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
媒体:凝聚态物理的研究都为人类带来过哪些新发现?对物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哪些突破?
丁洪:近代科技的突破跟凝聚态物理相关,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晶体管,第二就是巨磁效应的实现,还有超导体。凝聚态物理对科学范式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创造了一种“More is different”的思维方式。
媒体:您目前最关注的科学问题是什么?
丁洪:我们目前最关注的是拓扑量子计算,我希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拓扑量子比特。
媒体:您理想中的量子计算机应该是什么样的?
丁洪:它的功能跟现在的计算机相比,计算速度几乎是快无穷倍,现在无法解决的事情对它来说都不是问题,比如破译密码、预测天气和发现新药等。
用经典计算机去模拟量子世界,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只有用量子计算机才可以,所以要探索宇宙奥秘,最终还是要依靠量子计算机。
媒体:超导在生活中的应用有哪些呢?
丁洪:应用比较多是医院里的核磁共振,高档的都是超导体做的。超导主要是做两方面,一方面它是用来做信息材料的。比如实现量子计算,现在主流的量子比特要用超导,我们做拓扑量子计算也是用拓扑超导体,所以量子计算最终大概率是依靠超导体。超导应用的另一方面是能源材料,比如核聚变,因为核聚变的实现往往用磁场去约束,而强磁场是需要高温超导体的。
媒体:拓扑超导和超导量子比特差异是什么?
丁洪:主要差异是具有天生的容错性,用拓扑保护来使量子计算不容易受外界的干扰,出错率大幅度降低。理论上是非常好,但问题是现在一个拓扑量子比特都没造出来,它不像超导比特现在可以造出来几百个。我希望拓扑量子比特在5年之内出现,我们现在也在紧锣密鼓地冲击这个目标。
媒体:人工智能加速了学科融合,未来学科分类会不会因此改变?
丁洪:为什么会有学科分类?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因为人大脑的容量太有限。当人们发现人脑装不下所有知识时,就需要数学、物理、化学分开学。但有了AI以后,什么知识都能装得下,也许AI就不需要学科分类。未来人在AI的帮助下,也许在30岁前既是物理博士又是生物博士,还是计算机博士,这种高质量的模式,现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运营编辑 | 曹倩 审核|孟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