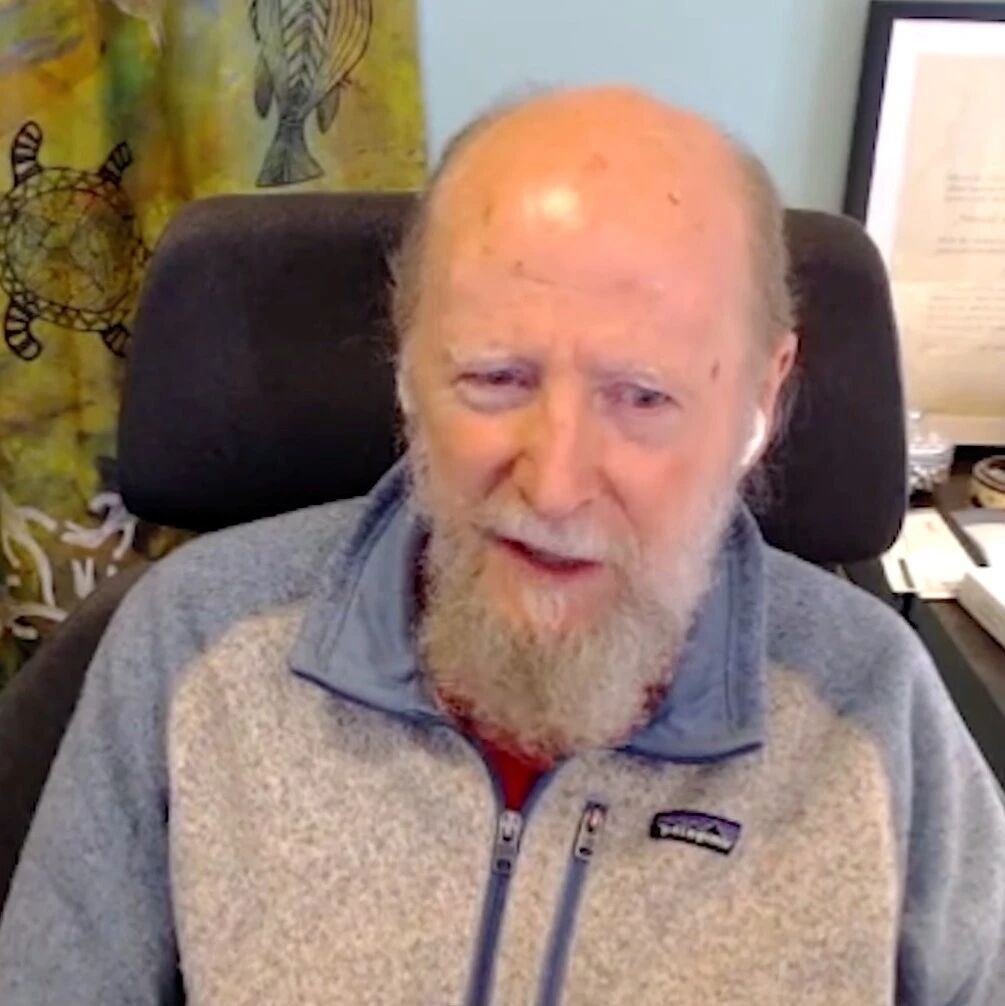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2025年初,美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连续发布多篇关于AI与半导体出口管制的研究,系统梳理了美国盟友在法律权限上的差异,并揭示出一个长期困扰政策界的悖论:过度管制可能损害本国产业利益,而管制不足则可能导致战略防线失守。在这一背景下,CSIS的分析逐渐指向一个新的政策重心:半导体制造设备(SME)。与广谱芯片限制相比,设备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更强的“扼喉”特征,既能对前沿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环节形成有效约束,又能相对减少对民用和下游产业的连带伤害。更重要的是,欧美日等国在设备领域的市场份额与技术优势远大于在通用芯片上的主导力,这为跨国协同提供了现实杠杆。由此,设备环节逐渐被视为在“安全—产业—可执行性”三角之间实现平衡的政策焦点。本文将结合CSIS的分析,探讨盟友权限的结构性差异、美国出口管制政策辩论的核心分歧、全球连锁反应以及未来可能的战略应对路径。
美国凭借《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实体清单”以及“U.S. Persons Rule”等强力工具,构建了一个兼具域外性与名单化的管制体系。历史上,伴随着美国对于出口管制等限制性工具的常规性使用,美国已建立以出口管制局为代表的完善机制和执行机构,形成法律和执法的闭环。然而,CSIS研究显示,美国多数盟友并不具备类似权限,其法律框架大多局限于特定清单或单项许可制度。表面上,这使得它们在执行范围与执法力度上远弱于美国。
然而,差异化并不等于空白。欧盟在《2021/821号条例》第9条下允许成员国以公共安全或人权理由实施单边管制。荷兰据此对EUV光刻机等先进设备设立许可要求,早在2019年就停止批准对我出口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并在2023年和2025年多次收紧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日本则通过《外汇外贸法》将23类半导体制造设备纳入管制清单。可见,在先进芯片与制造设备(SME)领域,盟友实际上拥有相对集中的操作杠杆。在《理解美国盟友在实施出口管制上的现行法律权限》一文中,作者正确地认识到没有“美式FDPR”并不等于不能控,只是行动需要更多政治意愿与执法资源的支撑,而能够积累足够的政治意愿往往取决于美盟友如何“独立地”看待产业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当前美国出口管制政策辩论的核心在于“过控”与“欠控”的平衡。若过度管制,势必削弱企业规模经济与研发资金来源,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受损;若管制不足,则容易被对手通过转运、再出口、服务外包等途径绕过,从而丧失战略防御。在美国对华发动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之下,天平的平衡已经倾向于扩大国家安全范畴,并将产业利益作为国家战略利益的附庸。但是,这种零和思维在美同盟国家中未必具有同等吸引力。
《出口管制:持续不断的长期争论》站在历史视角下重新审视这一两难,认为这一争论并非新现象,而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博弈的周期性回归。近年来,美国及盟友在“友岸外包”和“可信伙伴”概念下尝试重构执行框架,但执行边界往往高度模糊,以至于未能达到“全面技术封锁”的既定目标。例如,中东部分国家虽然不是美国对手,但其再出口与转运风险多次引发其执法担忧。CISS提醒,政策制定者必须在战略防御和产业利益之间找到动态均衡,而非寄望于“一刀切”的解决方案。
在这一张力下,现实路径逐渐回到“逐项—逐国—逐案”的审单逻辑。文章强调,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实践逐渐从宏大的口号回到更为琐碎而现实的执行逻辑:每一类产品、每一个目的国、甚至每一个终端用户,都需要逐案审查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出口管制的有效性并非取决于一纸制度,而是依赖日常执法与跨部门协调的持久投入。美国虽强调“友岸”与“可信伙伴”,但CSIS提醒:伙伴的可信度并非天然,而是动态评估的结果。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因再出口与转运问题而被执法界视为高风险地区,说明“盟友即安全”的等式并不成立。由此可见,过控/欠控并非静态选择。
基于情景的精细化出口管制需求无疑对技术手段和策略提出了新要求。美精挑细选的卡脖子关键领域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出口管制品必须具有强战略性,对于半导体制造或AI训练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其必须属于美及其关键盟友(欧盟、日本、韩国)的绝对优势领域;最后,美出口管制局等执法机构必须具备对该管制物项进行明确溯源的技术手段和数据储备。并非所有硬件设备均满足以上三条件。
面对“过控/欠控”的长期困境,《国家安全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将政策重心引向半导体制造设备(SME),并提出这是实现战略与产业平衡的关键切入点。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设备在全球半导体生态中的特殊地位。与先进芯片相比,制造设备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上游,被普遍视为“卡脖子环节”。全球产能高度集中在美国、荷兰、日本三国,这使得它们在协同推进管制时具备天然的市场支配力和技术优势。换言之,只要在设备口径上形成最小共识,就能够对全球高端算力发展施加显著影响。就目前而言,荷、日两国均展现出较强的追随意愿。尽管时任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和贸易发展合作大臣Reinette Klever均表态称限制出口并非“刻意”与美国保持一致,其积极滚动更新清单,并对我不断加码口径限制的行为是难以辩驳的。
第二,设备管制的外部性相对较小。广谱性的芯片禁令往往波及范围极广,容易冲击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与军民两用关联度不大的下游产业,从而在国内引发产业界的强烈反弹。而针对制造设备的定向限制,则更直接地作用于对手构建前沿产能的能力,对普通民用产业的副作用有限。这种“聚焦扼喉点”的方式,能在有效抑制军民两用扩散的同时,降低对本国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伤害。2025年,在荷兰再次通知自4-01起收紧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时,行业巨头ASML跟进表态称此举对业务的影响有限。
最后,设备管制具备更强的制度可操作性。荷兰对EUV光刻机出口许可的限制、日本对二十余类设备的纳入管控,以及欧盟《2021/821条例》第9条提供的法律依据,都为这一政策路径提供了可参照的实践经验与法律锚点。这意味着,美国与盟友完全可以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通过建立“共同清单”和“统一许可基线”来实现政策的快速落地与持续执行,而不必重新设计一套复杂且可能引发法律争议的新机制。早在2024年,ASML就已加强了与政府的政企协同,在荷兰政府宣布扩大国家层面的设备出口许可范围时同步表示该举措属于“技术性调整”。可见,当荷兰和日本等美传统盟国政府与当地主要企业达成一致后,管控关键硬件的出口流向相对容易实现。
综上,设备优先战略不仅能够发挥上游控制力的杠杆效应,还能在安全效能、产业代价和执行可行性三方面实现动态平衡。正因如此,CSIS认为这一选择是应对“过控/欠控”悖论的现实解法,也可能成为未来多边出口管制协同的最核心支点。
根据上述信息,美国以及其盟友未来的政策走向将围绕三个方向展开,并在“共同基线—联动机制—执行稳定”三个层面形成递进式的制度化演化,意在基于我已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大背景下进一步阻碍我半导体制造系统的发展速度和削弱技术潜力。
共同基线
在半导体设备、先进芯片节点以及高带宽内存、先进封装等核心环节,美、欧、日、韩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达成一致。尽管共同基线不需要追求完全统一的法律文本,但其势必要在关键设备目录、先进节点阈值以及端用/端用户定义上设立一套最低可比标准。这样做的核心目的,是防止由于各国政策表述与法律口径差异而产生“灰色空间”,被市场主体利用进行套利和规避。例如,如果美国将某一类先进封装设备列入许可清单,而欧盟未同步执行,企业可能通过转运或再出口将其绕过管制。建立共同基线,有助于将这种口径差压缩到最低。
联动机制
仅有共同基线还不足以应对快速演化的技术与市场环境。未来可能出现替代流、规避路径,甚至新兴技术绕过既有规则的情况。因此,CSIS建议建立一种动态触发条款:一旦任何一方发现违规或替代性流通渠道,就可立即触发联席复核与并行修订。这种机制意味着,出口管制从静态清单转向动态迭代,缩短政策与市场之间的时滞,减少“补漏洞”式监管的滞后性。它也将强化联盟内部的信息共享,提升执法行动的灵活性与前瞻性。需要强调的是,联动机制正常运转的关键前提是美及其盟友需要建立庞大且深入的数据交换系统和预警机制,目前尚不清楚多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就此达成一致。
执行稳定
政策的可预见性是产业界最为关注的部分。研究显示,科技政策的频繁调整和模糊口径往往导致企业陷入“合规迁徙”,将研发和生产环节转移到监管环境更加宽松的地区。因此,未来的政策重点之一是提升执行稳定性。这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发布许可统计数据,公开审批率与案例型指南,甚至设立季度执法公报,使市场对政策动向形成合理预期。通过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可以减少产业的不确定性成本,也能降低规避和套利的动机。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私人企业依然拥有着在人工智能训练和半导体设计方面的巨大投资额和因此带来的研发优势。在中短期未来,轻微的政策波动不会让跨国企业放弃将美国持续作为投资的头号选择。
从我方角度出发,这一趋势正在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美政策的精细化和制度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因此,我方必须建立覆盖“权限—执行—意愿”三维的动态数据库,持续跟踪各国在设备、服务与人员管制上的具体差异与变化。同时,应在高带宽内存、先进封装、光电集成等关键环节提前部署替代方案与冗余设计,避免在当前出口国进一步收紧政策时遭遇“断点风险”。换言之,我通过技术储备与产业布局来掌握主动空间的大方向仍然是最符合我国国情和战略利益的不变方针。
盟友出口管制的权限差异与“过控/欠控”悖论,既揭示了美国难以单边维持长久优势的制度现实,也说明“算力霸权”不可能靠一纸法令而得以无限延伸。在这一背景下,设备优先、基线协同与执行稳定,或许将成为未来多边出口管制的三大支柱。对我方而言,这既是外部约束,更是识别缝隙、谋求国产替代与内部赋能的战略机遇。在外部环境愈加收紧的前提下,真正的战略主动权不在于等待规则松动,而在于利用差异化执行的“时间差”和“空间差”,并在国际秩序层面提出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新规则与新范式。只有如此,我国才能在“算力霸权”与多边管制的夹缝中,争取到自身的战略回旋余地与长期发展空间。同样的,只要我国“苦练内功”,以我为主,美出口管制手段也无法在长期阻止我技术突破。
主理人丨刘典
编辑 | 张朔宁(达特茅斯学院)
排版 | 李森(北京工商大学)
审核 | 梁正 鲁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