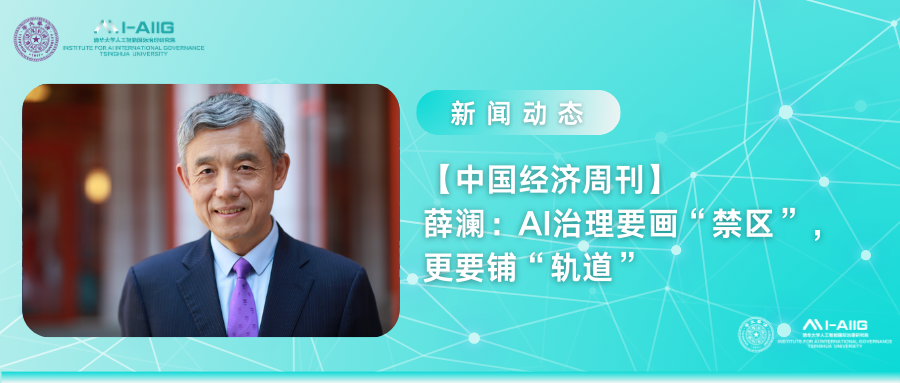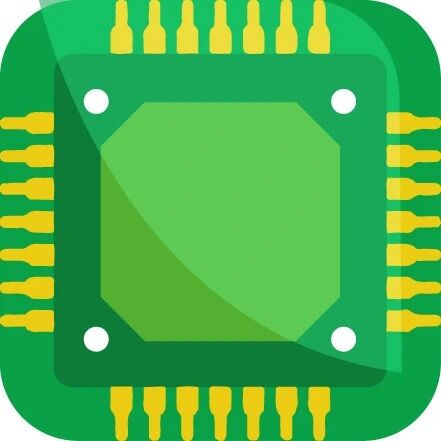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宣布共建“AI应用合作中心”,标志着非西方AI技术联盟的正式起航,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旨在全球AI版图中构筑独立“第三极”的重大战略行动。然而,在宏大的地缘战略叙事之下,该合作框架面临更为根本且棘手的内部挑战,即技术标准与互操作性的巨大鸿沟。本文深入剖析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因迥异的技术传统、破碎的数据基建、多样的法律框架以及复杂的语言文化所共同构成的困境。报告将详细论述,该协作中心若想取得实质性成功,必须在数据层、模型层、算力层和治理层四个维度上进行长期磨合。通过对每个层面具体技术难题的拆解,上合组织AI合作的未来,取决于其能否在内部建立起一套统一、高效且获得所有成员国信任的通用技术语言与标准体系。这一过程的艰难程度,将直接决定其“非西方AI范式”的真实成色与全球影响力。
从峰会宣言到“数字丝路”的战略铺垫
上合组织的AI合作建立在一系列已有的政治共识和合作倡议之上。梳理近年来的官方文件,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从2022年《撒马尔罕宣言》强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到2023年《新德里宣言》重申“保障各国在数字发展方面的平等权利”,上合组织已在顶层设计层面形成了反对“技术霸权”、追求“数字主权”的集体政治立场。这些宣言虽未专设AI章节,但其为AI领域的合作扫清了政治障碍,并确立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核心原则。
中国是推动这一议程的核心力量。2023年,中国正式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该倡议的核心思想,如尊重各国主权、反对利用AI谋求霸权、支持发展中国家参与等,与上合组织的集体立场高度契合,实质上为上合组织未来的AI合作提供了理论蓝图和话语体系。2025年中国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构建开源共享、和谐共赢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前后两个文件,从“倡议”走向“行动”,彰显了中国对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系列文件将AI治理与发展权、主权平等、技术共享等议题相绑定,强调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平等利用AI实现发展权利。

图1:外交部官网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倡议》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已与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特别是中亚国家)开展了广泛的“数字丝绸之路”项目合作。这些项目涵盖了5G网络、智慧城市、电子商务和数据中心建设,为未来AI应用的落地部署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例如,华为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项目,已在事实上输出了中国的技术标准和AI应用模式,为更高层级的AI合作进行了前期“压力测试”。这些真实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基础表明,上合组织的AI合作议程正在稳步推进,其最终目标是形成一个有别于西方的、自给自足的技术生态。

图2:中国-东盟AIGC大会
核心战略动因
要理解上合组织AI合作本质,必须将其置于当前全球技术地缘政治的宏大背景之下。其最根本的驱动力,源于成员国特别是中俄对陷入“数字附庸”地位的深层战略焦虑。在当前由美国主导AI生态中,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三重依赖,即算力依赖,顶尖AI算力(如Nvidia的GPU)被美国严格控制,并通过出口管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模型依赖,最强大的基础模型(如GPT系列、Claude系列)均为美国公司闭源产品,其API服务条款、定价权和技术演进路线完全由美方主导;以及生态依赖,从开发框架(PyTorch)到开源社区(Hugging Face),再到技术标准,整个AI技术栈“操作系统”几乎完全由美国科技生态定义。

图3:英伟达发布全新L40S GPU
任何国家若完全依赖这一生态,其数字经济的命脉便被掌握在他人手中。上合组织的AI合作,正是一次旨在打破这种单极依附关系的集体战略突围。其核心目标并非在短期内与美国进行对称的技术竞赛,而是要通过集体协作,构建一个内部循环、自主可控的AI技术与产业体系,从而捍卫和实现成员国在AI时代的“技术主权”。这一主权不仅包括技术上的自主选择权,更包括数据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发展路径的自主决定权。目前上合组织的AI合作战略精准对接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诉求,在发展AI时面临的三大痛点,即缺资金、缺算力、缺人才。美国的闭源MaaS模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可能加剧其技术依赖。
因此,全球AI的未来,将不再是美国一元主导的单极世界,而是正加速走向一个更多元、更多选择的多极化格局。由上合组织推动的AI“应用合作中心”,其核心竞争力不在于短期内能在基础模型性能上超越美国,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主张和发展范式。它以集体技术主权对抗技术附庸,以场景价值创造对抗算力军备竞赛,以发展权优先对抗价值观壁垒。美国AI产业的驱动力在于推出更强大的基础模型,而上合组织的合作模式则是“场景为中心”的应用。
战略层磨合:与技术现实的巨大落差
上合组织宣布共建“AI应用合作中心”,其战略愿景令世界瞩目,通过集体力量,在公共安全、跨境物流、能源转型等领域打造一个共享的、独立于西方的AI应用生态。目前严峻的技术现实跃然浮现,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技术异构性。这种异构性根植于各国过去几十年不同的信息化发展路径。尽管政治意愿强烈,但在实际操作层面,AI合作(特别是需要大规模数据共享的深度合作)直接撞上了各成员国日益强化的“数据主权”法律高墙。这构成了当前最核心的内部矛盾。
作为上合组织的引擎,中国建立了以国家安全为绝对优先的数据治理体系。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了严格的数据分类分级和跨境流动管制框架。在这之中,数据被视为国家核心资产,任何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数据共享都受到严格限制。
俄罗斯的信息化发展路径则依托传统的地缘政治框架和主权互联网。通过持续推广2019年通过立法提出的“主权互联网”概念,俄罗斯将其作为一种控制工具,将其作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数字出口产品。在成员国的数字化议程框架下,俄罗斯推动统一的数字标准、海关和物流平台,将该地区纳入其监管框架。此外,俄罗斯还利用语言和文化上的接近性,扩大其生态系统的覆盖范围。尽管俄罗斯在硬件方面不及中国,在投资方面不及西方,但其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监管和平台影响力依然显著。
印度作为组织内的主要大国,其数字治理逻辑截然不同。2023年通过的《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案》(DPDPA)虽然也赋予了政府广泛的权力,但其立法过程充满了公开辩论,并受到来自最高法院关于“隐私权”判例的制约。印度科技界和公民社会对大规模数据共享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因此,印度在任何上合组织的AI合作项目中,都将成为数据隐私和个人权利保护的“强硬派”,其法律除此之外,印度政府开发了印度栈(India Stack),这是一套开放的数字平台(Aadhaar、UPI、DigiLocker),为数千家初创企业和服务提供平台。这使印度在数字支付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并创造了开放数字化的典范。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虽在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但在数字治理立法上仍处于发展阶段。它们一方面渴望引入中俄的AI技术以促进经济和加强社会治理,另一方面也对其数字主权被过度渗透抱有顾虑。在实践中,它们往往会采取一种“选择性跟随”的策略,在具体项目上与中俄合作,但在建立全面、制度化的数据共享机制上则会保持谨慎。以哈萨克斯坦为例,通过建设数据中心或者枢纽,中亚国家可以获得更为突出的人工智能红利。阿斯塔纳枢纽已成为区域数字交通枢纽,并得到了Silkway加速器(与谷歌初创企业合作)、Hero Training和Scaler等加速器以及一支1000万美元的新创投基金的支持。其初创企业与全球风险投资网络建立联系,并参与Digital Bridge、硅谷驻留项目和AlchemistX等国际项目。阿斯塔纳枢纽正逐步从一个地方科技园区发展成为吸引人才、投资和出口潜力的磁石。
图4: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新突破:支持五种语言视频翻译,绘制民族风格图像(来源:哈萨克国际通讯社)
目前各国的治理现状显示,上合组织内部的数据流动面临多国多制”的碎片化格局,这使得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数据共享平台变得异常困难。这一过程将触及各成员国现有IT资产的改造,牵涉巨大的经济成本和部门利益,其难度不亚于一场深刻的内部改革。
模型层磨合:“信任赤字”与评估体系的缺位
数据层作为基础砖块填充人工智能,模型层则作为人工智能合作的建筑图纸。上合组织AI合作的第二个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建立成员国之间对彼此AI模型的技术信任。在上合组织内部,目前的挑战具体化为:如何从制度和技术上,确保一个成员国提供的“技术公共产品”不会成为另一个成员国的主权风险。
中国承诺将推广其先进的开源大语言模型。然而,当由中国企业开发的开源模型(例如,基于百度“文心”或阿里“通义”的某个版本)被提议作为协作中心的基础模型时,其他成员国,特别是俄罗斯和印度,必然会提出技术安全问题。
首先是算法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模型是如何训练,训练数据集中是否包含了可能对本国产生偏见的内容?模型的决策逻辑是否清晰可解释,还是一个无法穿透的“黑箱”。对于一个用于公共安全领域的AI模型,如果其关键决策逻辑无法被有效审计,任何成员国都难以放心采用。
其次是潜在的“后门”与安全漏洞。即使模型是开源的,其复杂的代码中是否可能隐藏着难以察觉的安全漏洞或数据上传“后门”?谁来负责对这些开源模型进行独立、公正、且技术能力足够强大的安全审计?这是极其敏感的信任问题。
再次是性能评估的“度量衡”统一。目前,全球AI模型的性能评估基本由美国的基准(如Super GLUE、MMLU)和平台(如Hugging Face的排行榜)所主导。上合组织若想建立内部的技术信任,就必须摆脱对西方评估体系的依赖,创建一套属于自己的、符合其应用场景需求的《SCO模型性能与安全评估基准》。这个基准不仅要测试模型的语言能力,更要侧重于其在多语言环境(特别是俄语、波斯语、印地语等)下的表现,以及在处理低质量监控数据、模糊卫星图像等真实应用场景下的鲁棒性。建立这样一个权威的评估体系,其难度不亚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学术评价中心。
模型层磨合:“信任赤字”与评估体系的缺位
第一,算力资源的极度不均。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并通过“东数西算”工程进行国家级统筹。俄罗斯拥有以Yandex和Sberbank为代表的本土云计算巨头。印度也在大力发展其数字基建。但中亚各国的算力资源则相对匮乏。这种“算力孤岛”现象,使得大规模的跨国联合训练变得异常困难。需要数千张高端GPU卡才能训练的先进模型,无法简单地将任务分散到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的多个国家。
第二,网络带宽与延迟的物理限制。从塔吉克斯坦的数据中心到中国的超算中心,海量数据传输所面临的跨境网络带宽瓶颈和物理延迟,是无法通过软件轻易解决的。这直接影响了分布式AI训练和实时推理应用的可行性。要实现真正的算力协同,上合组织需要投资建设一条专用的、高带宽、低延迟的“数字中亚高速公路”,其工程量和协调难度堪比实体的交通基础设施。
第三,算力主权的敏感性。算力不仅是技术资源,更是战略资产。让一国的关键数据(如边境监控数据)传输到另一国的超算中心进行训练,涉及到极其敏感的数据主权问题。任何一个成员国都难以完全接受其核心数据离境进行处理。因此,“AI应用合作中心”必须探索创新的技术模式,例如联邦学习,即“数据不动模型动”,让模型在各国的本地数据中心进行训练,只交换加密后的模型参数。然而,联邦学习技术本身尚不成熟,在超大规模模型上的应用仍面临效率和效果的巨大挑战。
治理层磨合:“法律迷宫”与集体规范的构建之难
最终,所有技术层面的互操作性挑战,都汇集到了治理层面。上合组织AI合作的终极困境,在于如何穿越由各成员国迥异的法律、文化和政治制度所构成的“法律迷宫”,形成一套真正具有约束力的集体规范。
首先是隐私保护标准的冲突。欧盟的GDPR影响了全球对个人数据保护的认知,但上合组织内部对此的理解和立法实践差异巨大。俄罗斯有其严格的《个人数据法》,要求数据服务器必须在境内;印度的《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也在不断演进。如何定义“个人数据”,如何界定“合法处理”的边界,如何在跨境数据分析中确保对各国公民隐私的充分保护,将是该组织联合伦理框架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其次是内容审查与算法监管的红线。对于AI生成内容的监管,各成员国的“红线”各不相同。一个在印度被允许讨论的宗教或政治话题,在其他成员国可能属于高度敏感内容。协作中心开发的任何具有内容生成能力的AI应用,都必须设计一套极其复杂且能够动态适应各成员国法律的“可插拔式内容过滤系统”。同样,对于算法推荐的监管,各国政府的介入意愿和力度也不同,这使得统一的算法透明度或公平性要求难以落地。
再次是责任归属的法律真空。当一个由多国数据训练、在A国部署、由B国公民操作的AI系统做出错误决策并造成损害时,法律责任应由谁承担?是算法提供方、数据提供方、部署方还是操作方?这种跨司法管辖区的责任链条认定,是当前全球AI法律界面临的共同难题,在上合组织这个主权意识极强的多边框架内,将变得尤为棘手。
面对难以在短期内逾越的法律鸿沟,上合组织正在采取一种更为务实和渐进的策略,试图从法律的“硬约束”之外寻找突破口。
第一,“标准协同”优于“法律统一”。鉴于统一立法几乎不可能,推动成员国在AI技术标准、安全规范和伦理指南上进行协同,成为更具可行性的选择。例如,可以共同制定针对特定领域(如人脸识别、智慧交通)的AI应用技术标准和安全评估指南。通过推广共同的技术标准,可以在事实上形成一套治理规范,引导成员国的AI产业朝同一方向发展,实现“事实上的统一”。这既尊重了各国的立法主权,又为未来的技术对接和系统互操作性奠定了基础。
第二,“应用场景”驱动合作。选择政治敏感度较低、经济效益明显的领域作为合作的突破口。例如,跨境电商物流、农业溯源、气象预测、能源互联网等领域。在这些场景下,数据共享的需求更具体、范围更可控,更容易获得各国立法和监管机构的许可。通过在这些领域打造成功的合作样板,可以逐步积累互信,为未来在更敏感领域的合作探索模式。
第三,强化“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开源AI平台和算法库的共建共享。中国正积极推动国内的AI开源社区发展,如百度的飞桨(Paddle Paddle)、华为的Mind Spore等。将这些经过市场检验的开源平台向SCO成员国推广,可以有效降低它们的技术门槛,并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基于共同技术栈的“朋友圈”。这种以开源为核心的“软基础设施”战略,是一种更巧妙的生态构建方式,它绕过了敏感的硬件和数据问题,从技术生态的底层构建向心力。
上合组织宣布共建“AI应用合作中心”,无疑是在全球AI地缘政治棋盘上落下的重要棋子。它清晰地表明,非西方世界正在集体探索独立自主的智能化道路。其背后的核心战略意图是通过集体力量,摆脱对西方AI技术生态的依赖,实现成员国在智能化时代的“技术主权”。上合组织正以“发展与安全”为核心价值,通过推广应用驱动的开源模型与构建国家主导的治理范式,系统性地打造一个有别于美国“市场霸权”和欧盟“规则霸权”的“非西方AI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以其对国家主权的高度尊重和对具体发展需求的精准回应,正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强大吸引力,其最终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争夺AI技术路线、治理标准和伦理叙事的话语权,从而深刻地重塑未来的多极化AI世界秩序。

图5:中国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建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来源:中国政府网)
这一过程的推进,将是对上合组织作为一个政治与经济共同体内部凝聚力和执行能力的终极考验。如果成功,它将真正锻造出一个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全球影响力的“非西方AI范式”;如果失败,所谓的“合作”则可能仅仅停留在象征性的项目层面,无法形成真正的集体力量。上合组织AI合作框架的成败,短期内并不取决于其能否立刻开发出匹敌西方的顶尖应用,而在于其能否在内部,通过艰苦卓绝的谈判与协作,成功构建起那套属于自己的、统一的技术语言和标准。这包括:一个统一的数据协议、一个可信的模型评估体系、一个协同的算力网络以及一个兼容各国法律的治理框架。
主理人|刘典
编辑 | 徐浩森(浙江大学)
排版 | 彭昕彤(北京外国语大学)
终审 | 梁正 鲁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