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诞生于洛杉矶仓库的SpaceX,现已成为全球商业航天的领军企业。其成功不仅催生行业爆发式增长,更引发学界研究热潮:学者通过解析技术优势、管理模式与运营路径,试图提炼可复制经验,如孙美玉等剖析商业模式,范艳清等从质量管理架构切入总结特色模式。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其商业化路径,对政企互动关系探讨不足,仅韩颖琦等简要梳理政府支持,但也缺乏双向互动分析。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 SpaceX和美国政府合作的解读,以弥补相关的研究空白,为中国在航天领域构建新型的政企合作关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太空霸权的争夺贯穿了美国的航天发展史:早在 1955 年,美国便提出了 NSC5520卫星项目,但苏联的 Sputnik I 号却夺走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头衔。作为回应,美国在 1958 年发射了 5 颗卫星,并 推 动 国 家 航 空 咨 询 委 员 会(NACA)改组为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使得太空争霸走向体系化。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落后于苏联的事实——1961 年,Yuri Alekseyevich Gagarin 又成为了进入太空的第一人。随即,美国实施了阿波罗计划,成功地将阿姆斯特朗(Neil Alden Armstrong)送上了月球,而苏联由于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逝世等因素输掉了竞赛,美国借此确立了太空霸权。但新的竞争又很快出现:1980 年欧洲成立了阿里安航天公司(Arianespace),该公司致力于提供商业航天发射服务,从而在航天开辟了新的竞争领域。为了实现全方位的领先,美国政府决定引入私营公司构建成本优势,并以《国家航天政策》(《National Space Policy》)鼓励商业航天。而这种“经济式”的霸权思维让 SpaceX 有机会进入这个被政府一直垄断的领域,也塑造了其可重复、低成本的运营理念。
首先是来自欧洲的挑战。阿里安公司成立后,不仅抢占了美国公司 GTE Spacenet 的发射合同,而且其“独立进入太空,成为商业太空领导者”的目标更直接挑战美国霸权。所以,Ronald Wilson Reagan 政府于 1984 年通过了《商业航天发射法案》(《Commercial Space Launch Act》),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商业发射领域,为 SpaceX 的诞生奠定了法律基础。其次是航天飞机的自身困境。航天飞机单次飞行成本高达 5 亿美元,远超最初 3000 万美元的目标,且 30 年服役期内发生 2 次重大事故,致 14 名宇航员遇难。所以,高成本与高风险最终使其于 2011 年正式退役。最后是美国内部的需求。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年均太空发射量仍达 117 个,且商业发射持续增长,所以就急需 SpaceX 进场,以迅速占领市场。此外,其通过的《美国商业太空发射竞争法案》 (《 U.S. Commercial Space Launch Competitiveness Act》 )赋予个人或企业对太空发现物质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极大激发了美国人的探索热情,促使 SpaceX 等企业纷纷涌现,抢占市场。就此,美国的商业航天迎来了春天。
可见,SpaceX 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在美国霸权思维的影响下,对外竞争危机促成了国内的立法,同时航天飞机退役也留够了市场空白,给足了 SpaceX 发展空间。
SpaceX 之所以能在一众新兴的航天企业中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是其做到了与政策基调高水平对接,因而备受美国政府青睐。
首先,SpaceX 的低成本理念契合美国维持霸权的需求。Elon Reeve Musk 提出将现行太空探索成本降至原先 1% 的目标。因为航天发射门槛高,竞争者有限,所以一旦 SpaceX 实现了以超低成本进入太空,就会形成垄断地位,他国私营企业可能尚未成型就已经胎死腹中了,而这与美国所追求的霸权理念是高度契合的。其次,SpaceX 的私营身份为美国规避了诸多麻烦。1967 年签订的《外层空间条约》 (《 Outer Space Treaty》)规定各国政府不能在空部署武器 。 但借助 SpaceX 的私营外衣,美国正在实质性地推进太空武器部署的进程——2023年,SpaceX 为美军发射了导弹追踪卫星及 X−37B 飞行器,但基于 SpaceX 的私营属性,各国政府对这些行为也只能“缄口不言”。最后,SpaceX 重塑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其火星移民愿景犹如新时代的“哥伦布”,重绘了“美国梦”,这对于近些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失控、两党纷争、恃强凌弱而饱受诟病的美国政府来说无疑是“及时雨”般的存在。美国政府历来自诩为文明灯塔与科技领袖,而 SpaceX 所具备自由、科学、探索的精神恰好能与之对应上。故此,SpaceX 就成为美国对外宣传形象的“明星标本”了。
综上所述,便可得出其在政策领域的塑造与反馈的体系。即美国政府以霸权为路线指引,具体的历史情境为催化剂,孕育出了商业航天的政策基调,给 SpaceX 等私营航天企业带来了新生的机会。同时 SpaceX 也不负众望,在核心理念、舆论规避、形象塑造上给予美国政府积极的反馈,以实际的行动构建起美国在商业航天新的垄断形式:技术及价格的优势—占领市场—获取利润—投入新的技术—技术及价格的再次碾压。由此,美国得以先人一步,在商业航天领域树立起了新霸权。
在 SpaceX 的技术研发上,美国政府从人才、技术转让、现有设备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支持。
1) 在人才层面上,美国政府的帮扶呈现出了系统性、共享性与可持续性的特点。
首先是专业人才的系统支持。航天是高度集成的产业,作为初创公司的 SpaceX 难免会在许多系统性工程上“考虑不足”,如龙飞船生命支持系统需实现氧气、二氧化碳等多方面的平衡。对此,具备丰富系统整合经验的 NASA 工程师直接入场指导,助力龙飞船得以快速服役。其次是顶尖人才的共享流转。顶尖人才往往具有培育周期长、数量少的特点。对此,政府允许 SpaceX 直接聘请其内 部 专 家 。 例 如, 联 合 创 始 人Tom Mueller 来自发动机制造商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Thompson Ramo Wooldridge Inc);Chris Thompson 是“大力神”火箭的首席设计师;另据外媒报道,NASA 前高管 Kathy Lueders 退休后也加入 SpaceX。通过这种人才的共享模式,SpaceX 的研发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最后是未来人才的积极培育。美国通过融合国内高等教育体系和国际人才交流,为 SpaceX 等企业打造了持续性的人才供应。一方面,加州理工学院、 马 里 兰 大 学 等 在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开设了更多的航天专业,为 SpaceX 培育未来人才。另一方面,美国较为宽松的科研环境和丰厚报酬,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航天人才聚合于此。由此,SpaceX 的人才选择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展。
2) 在技术层面上,美国政府对 SpaceX 也是倾囊相授。
一是成熟专利技术的转让。如 SpaceX 的梅林发动机,就采用了 NASA 的喷注器技术。而随着登月计划的启动,美国政府加快了向 SpaceX 等伙伴的技术转让步伐。一方面,可以帮助 SpaceX 打破技术壁垒;另一方面,则压缩了相关技术的研发时间,加速其市场化的步伐。二是技术使用经验的共享。2023 年,SpaceX 开始与 NASA 合作开发集成的近地轨道架构。对此,NASA 的商业航天主任 Phil McAlister 直接表示:“这些公司可以利用 NASA 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而这样的经验授予便可使得 SpaceX 在技术上少走弯路,并促进双方人员的交流与技术创新。
3) 在设备层面上,美国政府则为 SpaceX 提供了全周期的发射支持。
首先,火箭发射前需要试验台测试发动机,而美国政府租借给 SpaceX 的麦格雷戈基地,直接留有贝尔公司(Beal Aerospace)现成的设备。此举无疑为 SpaceX 带来了成本、时间效益。其次,在发射时所需的平台上,美国政府也毫无保留,直接将肯尼迪航天中心的 39A 发射台、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的 40 号发射复合体,以及范登堡空军基地 4E 发射台租借给 SpaceX,以节省其开支,满足不同轨道的发射需求。最后,在发射后的测绘上,因为 SpaceX 的火箭发射后需要回收,必须实时测量火箭的位置并建立通信方可实现。为 此, FAA(联 邦 航 空 管 理 局 )、FCC(联邦通信委员会)、NOAA(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多部门联调回收测绘系统,实时追踪火箭位置并建立通信链路,保障火箭安全回收。由此可见,SpaceX 的成功与美国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首先,SpaceX 帮助美国政府解决了就业问题。随着航天飞机退役和 NASA 预算收紧,大量的技术人员面临再就业困境,且严格的劳工法律也限制了 NASA 的裁员空间。而 SpaceX 正好能够解决这些人的再就业问题,据统计,该公司仅 2022 年就新招了 2500 名员工,这与美国政府提出的“制造业回流”战略不谋而合。其次,SpaceX 助力美国政府获取新技术。NASA 资助发明虽归 SpaceX 所有,但美国政府享有协议框架下知识产权的永久免费许可。就此,创新能力不足的 NASA 便可用老技术换新技术,SpaceX 也节省了成本与时间。最后,SpaceX 帮助美国政府降低了产业成本。传统航天部件因产量低缺乏规模效应导致价格高昂,而 SpaceX 的目标就是把产品平民化和产业化,因而以往一次性的产品就可以重复生产,所以当 NASA 的某个技术产品向 SpaceX 开放时就可以降低价格门槛。例如,NASA 将酚醛浸渍碳烧蚀材料的技术转让给SpaceX 后,该公司改进配方实现产业化,使其价格降至原先 1/10,而依托共用产业链,NASA 自身制造成本也随之降低。
综上所述,便可得出双方在技术层面的互动关系。美国政府为 SpaceX 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在人才上,既共享顶尖专家又培育新力量;在技术上,通过转让技术与分享经验加速其创新;在设备上,各部门协调提供发射便利。SpaceX 则“投桃报李”:创造就业、拉动基建,并授权政府使用其新技术。通过这种深度合作,二者之间已经逐步走向共生、共享、共赢的新型合作之路。
在资金投入上,美国政府从开源、节流、兜底等层面对 SpaceX 进行了全方位的扶持。
1) 在开源方面,美国政府通过 合 同、 补 贴 、 贷 款 等 形 式 对SpaceX 提供支持。
首先,美国政府以服务合同的形式,为 SpaceX 提供了现金流。2008年,SpaceX 发射失败,资金链濒临崩溃,NASA 及时与其签订了 16 亿美元商业补给服务合同,使其摆脱困境。因此,美政府确实是 SpaceX 的“救星”。其次,美国政 府 还为 SpaceX 提 供 专 项 补贴。如在 2020 年 FCC 便以农村宽带建设为由,向星链注入 8.85 亿美元资金。得益于此,SpaceX 早已安全度过了投资大、周期长的前期阶段。最后,美国还利用强大的金融工具,为 SpaceX 提供多样化的融资。其中,进出口银行发挥了关键的角色,多次以贷款的方式支持本国航天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而政府的支持也使 SpaceX 获得了诸多资本的青睐与投资,有效解决了其融资难题。
2) 在节流方面,美国政府利用多样化的税收政策减轻 SpaceX 的负担。
首先是研发税收抵免。作为科技公司的 SpaceX,其研发费用无疑占比较大,而据《经济复苏法案》 (《 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和加州在 1988 年的研发税法案,SpaceX 可以享受到联税、州税两级研发费用抵扣。以税代赈,有效促进了公司资金向研发板块的投入。其次是财产税免除。加州于 2014 年通过 AB−777 法案,给予 SpaceX 10 年财产税豁免。2023 年,州长纽瑟姆(Gavin New-som)将该政策延长至 2028 年。此举显著降低了 SpaceX 运营成本。最后是以规明税。针对 SpaceX 跨洲发射业务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加州拟通过关于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法规,用于明确 SpaceX 等航天企业所交税款。这不仅可以简化税收程序,而且有助于 SpaceX 做好成本估算以预设发射价格,争夺国际市场。
3) 在保障方面,美国政府主要以商业保险为航天企业提供保障:1988 年修订的《商业航天发射法案》允许联邦航空管理局为重大灾难保险兜底,从而使得私人公司愿意承保相关业务。而这一政策对于经常发射失败的 SpaceX 来说相当友好,因为其可以极大减少因为发射失败而陷入资金困境的局面。由此,极大地增强了 SpaceX 等航天企业的抗风险性和存活韧性。
1) SpaceX 的崛起为美国制造业的振兴注入了活力。次贷危机后,美国意识到实体产业是维系全球领导力的根本,故自 Barack Hussein Obama 政府时期起就力推制造业振兴。鉴于普通工业品受高汇率制约缺乏竞争力,美国便将重心转向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而 SpaceX 所经营的航天业务正符合美国政府发展高端制造业的要求。据统计,SpaceX 外包加工商达 268 家(均为美国本土企业),覆盖热处理、电镀等 2070 个工艺节点。所以,通过 SpaceX 这样的一个企业,美国的多个产业节点都得以盘活,且随着 SpaceX 的扩张,相关生产企业也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响应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
2) SpaceX 的成功显著提振了美国金融业。其 1400 亿美元市值及《2023 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Hurum Future Unicorns in the World 2023》),第 2 的地位,使其成为投资者的“摇钱树”,成功吸引数十亿美元国际融资。这不仅抬高了对美国企业的投资热情,更巩固了美国的“投资热土”地位。同样,马斯克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其 6000 多亿美元的市值有效支撑了美国股市的繁荣,其中除了特斯拉汽车本身的成功外,也离不开 SpaceX 的助力——马斯克曾用火箭把一辆特斯拉的跑车送上了太空,这不仅带来了特斯拉股价的大涨,也对美股产生了积极的拉升效应,所以从金融业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对于 SpaceX 的投资是相当成功的。
3) SpaceX 增强了美国霸权的可持续性。美国对 SpaceX 的投资不仅能带来投资和税收,推动产业升级,其还会直接购买 NASA 产品、技术和专利,如肯尼迪航天中心的液氧、甲烷等。这就使得原先较为单一的投资收益路径得到了扩展,形成了可循环的收益体系。借此,NASA 便可以较低的成本完成维护航天霸主地位的政治任务。所以在阿尔忒弥斯计划中,NASA 便成为发包商角色,将载人登月合同外包给 SpaceX 等私营企业,利用其成本控制优势实现资金利用最大化,从而极大增强了航天霸权的韧性。
综上所述,便可得出双方在资金上的互动机制。即政府通过开源、节流、兜底等方式对 SpaceX 进行“保姆式”的扶持,而 SpaceX 则带来了制造业回流、金融业发展、霸权维系等多重收益。因而双方的合作确实是互利共赢的。
基于以上对 SpaceX 和美国政府合作的解析,为中国商业航天中政企关系的发展提供 8 点建议。
1) 搭建适当的合作平台,使得航天企业和政府之间有足够的交流空间。目前,虽然中国的商业航天企业发展迅猛,但却面临着缺技术、缺人才的局面,而中国的国家航天体系正好拥有丰富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因此,可以在不违背保密原则的基础上构建相应的机制平台,使得双方能够各取所需,促进技术与人才的流动。
2) 试点合同外包制模式,助力商业航天的初步发展。在国家的发射任务中,可以将一定比例的发射任务以合同的方式投放市场,进而为初创的航天企业提供一定的发展机会和启动资金。同时,在此过程中要探索此模式的监管方式,进而总结出符合中国国情,在商业航天领域政企合同合作的可行方案。
3) 强化政企双方在产业链上的协作,从而构筑航天产业的共享生态。在航天产业链的上游,双方可以采取联合采购的方式,进而降低原材料采购价格;而在产业链中游,对于通用型产品的制造,则可共享生产线以缩减制造费用;最后在下游,则根据市场和任务需求做出业务上的区隔,以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4) 逐步构建起政府资本筑基、企业创新反哺的太空经济循环体。针对商业航天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可以构建起一个阶梯式的资金支持体系,通过专项基金、产业补贴、税收减免、保险兜底等多重工具的综合运用,为商业航天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而企业在完成规模化运作之后,一方面,要继续履行好财税缴纳和吸纳人才的义务;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专利授权的形式反哺公共研发体系,从而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5)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让商业航天政企关系的发展有充分的合作法规依据。在合作深度、合作范围、合作方式上,都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政府和航天企业之间的合作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行动指南,这样才能使得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开放、更合规,进而在航天领域为政企关系的发展明确新道路。
6) 加强政企双方在精神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互惠关系的发展。一是企业要增强与国共生、共荣的意识,不做危害国家利益的事;二是在不泄密的情况下,政府为企业尽可能地提供便利,从而构建起政企双方长久、可持续、互惠互利的和谐关系。
7) 注重舆论的作用,维护政企合作的正当形象。中国的航天企业常被国外污名化,认为其不够商业化,和政府关系太过紧密。对此,可以通过 SpaceX 和美国政府之间密切的现实关系为由反驳相关言论,同时做好对外的宣传工作,从而为中国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全世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8) 倾听对方合理关切,寻求适当方式解决政企矛盾。合作过程中,政企双方有时可能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而产生矛盾,这些矛盾应该诉诸规则、市场、舆论、法律等手段等来解决,使得双方的矛盾限定在一定框架内,减小甚至消除相应事件对双方合作关系的影响。
SpaceX 与美国政府的合作是多维且双向的。政策上,美国政府以霸权理念引导 SpaceX,而 SpaceX 也推动了美国航天循环式霸权的形成。技术层面,双方优势互补,形成了互利共赢式的技术交流体系。资金方面,美国政府通过金融手段扶持 SpaceX,促进了制造业回流、金融市场繁荣,提升了航天霸权韧性,实现了投资效益最大化。这种成功的合作模式为中国商业航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有助于构建新型政企合作关系,实现航天强国梦想。
本文作者:卢俊先, 乔笑斐, 高策
作者简介:卢俊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乔笑斐(通信作者),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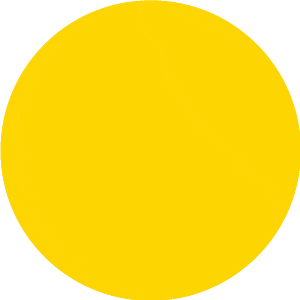

内容为【科技导报】公众号原创,欢迎转载
白名单回复后台「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