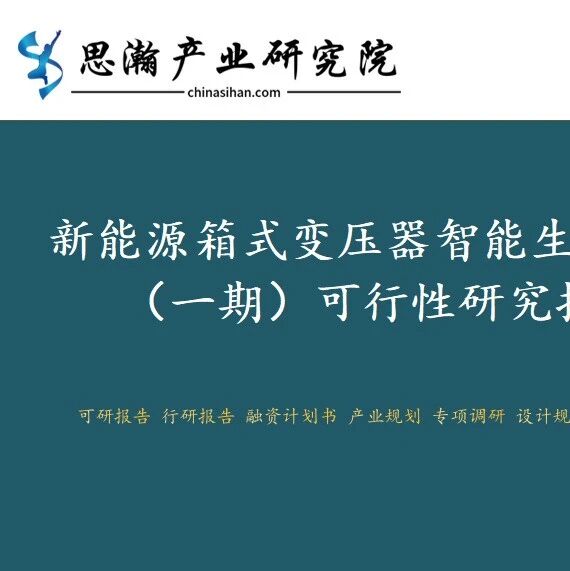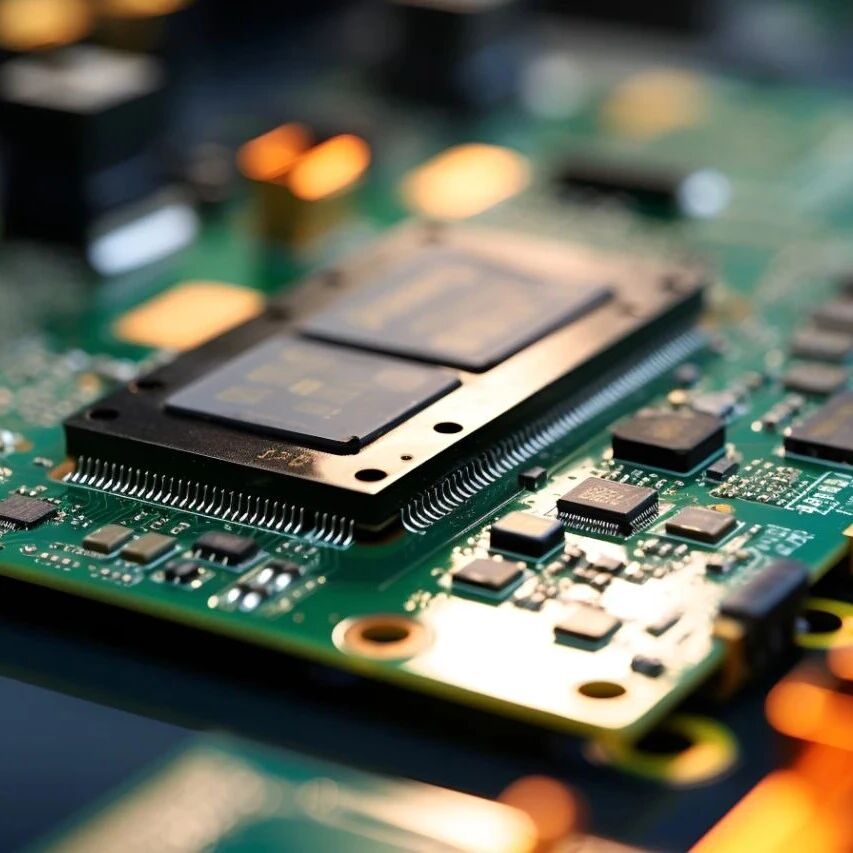在脸谱网和Reddit上,这些员工们交换了意见。以前,Shipt有一个公式,因此他们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多少:每送一单,员工会得到5美元的基本工资,再加上客户通过应用程序下单所支付总金额的7.5%。借助此公式,员工可以查看订单数量,选择值得花时间的工作。但Shipt在未通知员工的情况下改变了薪酬规则。公司最终就此变动发布新闻稿时,只透露了新的薪酬算法将根据“努力程度”来支付员工工资,其中包括订单数量、预计用于购物所需的时间和送货里程等因素。
Shipt公司声称这种新方法对工人更公平,并且能更好地匹配工资与订单所需的劳动力。然而,大多数工人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薪水在减少。由于Shipt并未公布算法的详细信息,因此它本质上是个员工无法看透的黑盒子。
工人们本可以默默认命,或者到其他地方另找工作。但他们并没有这样,而是联合起来,收集数据并与研究人员和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帮助理解自己的薪酬数据。身为一名数据科学家,我在2020年夏季参与了这项工作,着手打造了购物者透明度计算器这个基于短信的工具来收集和分析数据。在这个工具的帮助下,有组织的工人及其支持者对算法进行了基本审计,发现算法导致40%的工人大幅减薪。工人们的做法表明,反击不透明的算法权威、建立透明度是可能的,即使这与公司的希望背道而驰。

就在那时,索利斯联系了Coworker,这是一家通过帮助请愿、数据分析和开展活动来支持工人权益的非营利组织。时任Coworker数字宣传总监的德鲁•安布罗吉(Drew Ambrogi)把索利斯介绍给了我。当时我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但对前途感到失望。虽然我的研究侧重于从群体中收集数据进行分析,但却没有任何群体参与我的工作。我将Shipt案例视为与群体合作并帮助其成员控制和利用自身数据的一种方式。我一直在了解疫情期间零工快递员的经历,疫情让他们突然变得不可或缺,但他们的工作条件却每况愈下。安布罗吉告诉我,索利斯一直在收集有关Shipt工人工资的数据,却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数据。于是我发现了一个有用的方法。

以零工雇用为商业模式的公司有意保持算法不透明。这种“信息不对称”有助于公司更好地控制员工,即公司在不透露细节的情况下制定条款,而员工只能选择是否接受公司条款。例如,公司可以每周改变工资结构,通过一次次试探,找出可以在降低多少工资的同时仍然让工人接受工作。没有任何技术原因可以解释这些算法为什么必须是黑盒;真正的原因不过是为了维护权力结构。
对于Shipt的工人而言,收集数据是获得影响力的一种方式。索利斯发起了一个群体驱动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收集了很好的数据,但效率低下。我想实现其数据收集工作的自动化,这样就能更快、更大规模地收集数据。起初,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网站,让员工上传各自的数据。但索利斯解释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员工只需通过手机便能轻松访问的系统,他认为基于短信的系统将是最可靠的吸引员工的方式。
根据这些意见,我创建了一个文本机器人,任何Shipt的工人都可将自己的工资单截图发送给该文本机器人,并获得相关情况的自动回复。我用简单的Python脚本编写了文本机器人代码,并在我的家庭服务器上运行该代码;我们使用了Twilio来发送和接收文本。该系统使用了光学字符识别技术(与在PDF文件中搜索单词的技术相同)来解析屏幕截图的图像并提取相关信息。它从Shipt收集了有关工人工资、顾客小费、工作时间、日期和地点等详细信息,并将所有信息加入了谷歌电子表格。字符识别系统很脆弱,因为我对其进行了编码,以便在屏幕截图的某些特定位置查找特定信息。项目启动几个月后,Shipt进行了更新,工人的工资单突然看起来不一样了,我们不得不匆忙更新系统。
每个发来截图的人都有与其电话号码绑定的唯一ID,但我们只收集工人所在的都市区作为人口统计信息。虽然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分析工资水平是否与年龄、种族或性别等其他人口统计数据存在关联会很有趣,但我们希望确保员工的匿名性,这样他们就不用担心因参与了项目而遭到Shipt解雇。从技术上讲,共享相关工作数据违反了公司的服务条款;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自己的数据,包括被归类为“独立合同工”的零工在内的员工往往都不享有任何权利。

这种形式的“工资盗窃”并不显眼,因为在新方案下,60%的工人的收入水平较以往大致相同或略高。但我们认为,有必要让那些因黑盒手段、未被告知而遭受减薪的那另外40%员工了解到这一点。
除了薪酬公平,工人们还希望实现透明度和能动性。该项目突出了Shipt工人为获得这种透明所需付出的努力和搭建的基础设施,这需要积极进取的工人、一个研究项目、一名数据科学家和一个定制软件来揭示工人状况的基本信息。在一个更公平的世界里,工人应拥有基本的数据权利,法规会要求公司披露其在工作场所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相关信息,并默认信息对工人公开透明。

我们的研究并未确定新算法是如何得出支付薪酬的,但Shipt的技术团队在2020年7月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谈到了公司拥有的合作商店规模的数据,以及公司计算的购物者完成购物所需要的时间。我们最好的猜测是,Shipt新的薪酬算法估算了工人完成订单所需的时间(包括在商店寻找商品的时间和开车的时间),然后尝试每小时支付15美元的工资。被降薪的工人花费的时间似乎比算法预测的更长。
索利斯和他的盟友利用这些结果来吸引媒体的注意,他们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Shipt总部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塔吉特总部组织了罢工、抵制和抗议活动。他们要求与Shipt高管会面,但并未得到该公司的直接回应。Shipt公司向媒体发表的声明含糊其辞,只是说新薪酬算法会根据工作所需的努力来对工人进行补偿,并暗示工人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订单”。
抗议活动和新闻报道对工人的工作条件有影响吗?我们不知道,这令人沮丧。但我们的实验为其他想要利用数据进行组织的零工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范例,提高了人们对算法管理缺点的认识。我们需要的是平台商业模式的大规模改变。
一些关于零工数据权利的争论甚至走入了法庭。例如,2023年,英国的工人信息交易所赢得了针对Uber的诉讼,案件涉及了优步解雇两名司机的自动决策。法院裁定,必须向司机提供有关其被解雇原因的信息,以便司机能够对机器人的解雇决定提出有意义的质疑。
在美国,纽约市通过了全美第一部零工最低工资法,去年,DoorDash、优步和Grubhub对该法律提出了质疑,但以失败告终。在新法律出台之前,纽约市已经确定,其6万名送货工人的平均时薪约为7美元;新工资法将工资水平提高至每小时20美元左右。但该法律对零工工作中的权利失衡无能为力,并未提高工人决定工作条件、获取信息、拒绝监控或对决定提出异议的能力。
在世界其他地方,零工群体正在聚集起来研究替代方案。部分送货员已经开始了工人自主式服务,并加入了名为CoopCycle的国际联合会。有了这些平台后,工人们可以自行决定要收集哪些数据,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在印度尼西亚,快递员建立了“大本营”,在大本营,他们可以给手机充电、交换信息、等待下一个订单;部分快递员甚至建立了非正式的应急响应服务和类似保险的系统,帮助发生交通事故的快递员。
虽然Shipt工人反抗和审计的故事未能以童话般的结局收尾,但我仍然希望它能激励其他零工工人和工作时间日益受算法控制的轮班工人。这些群体即使想更多地了解算法如何作决策,往往也无法获取数据和技术技能。但是,如果他们思考自己对工作条件的疑问,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可以收集有用的数据来解答这些疑问。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有意将其技术技能应用于此类项目。
应该关注算法管理的并不只有零工。随着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更多的经济领域,白领们发现自己也受制于自动化工具,这些工具开始定义他们的工作日,并评判其表现。
新冠疫情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专业人士突然开始居家工作,部分雇主推出了可以捕捉员工电脑截图的软件,通过算法对员工的生产力进行评分。不难想象,在此基础之上,当前蓬勃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去向何方。例如,大语言模型可以梳理员工写的每封电子邮件和每条Slack消息,为管理者总结员工的生产力、工作习惯和情绪信息。此类技术不仅损害了人们的尊严、自主权和工作满意度,还造成了信息不对称,限制了人们质疑或商定工作条款的能力。
我们不能让事情发展到那样的地步。零工工人正在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作场所权利的更大战争的前线,将影响到所有人。现在是时候定义我们与算法的关系了。
作者:Dana Calac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