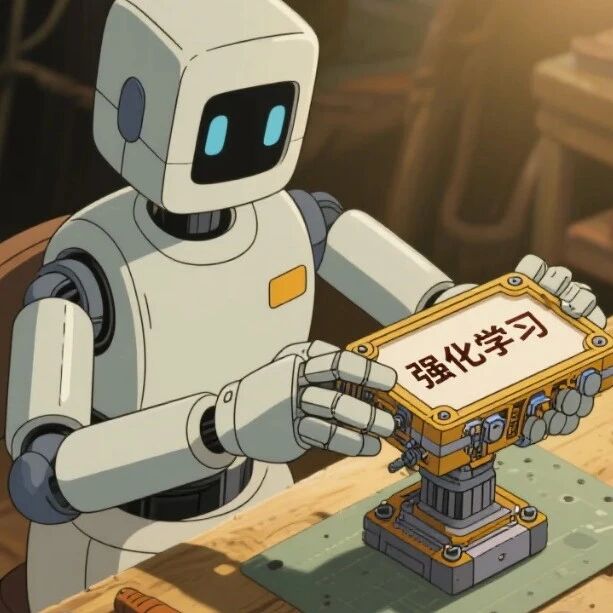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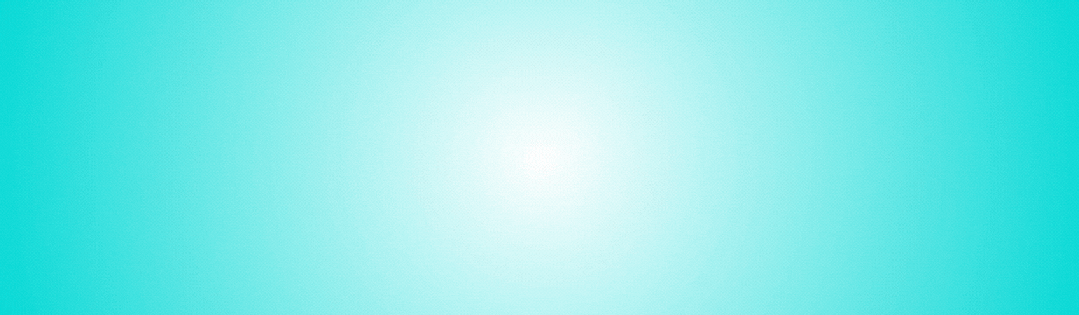
1.1重商主义的理论基础

图1 重商主义的核心
1.2重商主义的四大支柱
为了实现国家财富的持续积累这一最高目标,重商主义国家通过关税、补贴、殖民扩张和垄断特权,形成系统性政策组合。首先,贸易保护是其最核心的支柱。各国通过设置高昂的关税壁垒、实施严格的进口配额甚至直接禁止某些商品进口,来最大限度地抑制外国商品的流入。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出口退税、补贴等多种方式,不遗余力地鼓励本国商品销往海外,其唯一目的在于确保实现持续的贸易顺差,从而让黄金和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
其次,殖民扩张被视为实现重商主义目标的最高效路径。建立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不仅为母国提供了稳定且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使其摆脱对外国资源的依赖,更重要的是,殖民地被迫成为母国制成品的专属倾销市场,形成了高度不平等的宗主国-殖民地经济循环。
第三,授予垄断特权是国家与商业资本紧密结合的体现。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等被授予国家特许状的商业巨头,获得了在特定地区(如印度、东南亚)和特定商品(如香料、茶叶)上的贸易垄断权,它们作为国家的代理人,通过商业活动实现国家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目标。
第四,国家通过立法实施严苛的贸易管制,如英国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 1651–1673》)。该条例规定,所有进出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运载,并严禁殖民地发展可能与母国形成竞争的制造业,从而将殖民地永久地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当西班牙与葡萄牙为争夺香料群岛摩鹿加的控制权而兵戎相见,其背后的逻辑正是重商主义式的,即谁控制了肉豆蔻等珍稀香料的唯一产地,谁就控制了其全球贸易并攫取巨额利润。

图2 殖民时期的重商主义
1.3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2.1数字重商主义的内涵
在21世纪,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理念以新的形式复现,其数字经济政策被学界与政策分析界称为“数字重商主义”。与历史上那个致力于保护本国特定制造业或贸易公司免受外国竞争的传统重商主义不同,特朗普的数字重商主义展现出更为复杂和微妙的保护对象,它所极力捍卫的,并非仅仅是谷歌、亚马逊、Meta等几家科技巨头的市场份额,而是一种使这些巨头得以实现天文数字般利润的、独特的商业模式。这一模式通过社会成本外部化,将企业责任部分转移至用户和社会,从而维持企业盈利能力。这种新形式被以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称为“现代重商主义”(Modern Mercantilism),其本质是重商主义意识形态的复兴。全球策略师迈克尔·埃弗里(Michael Every)更进一步,将新版本的重商主义称为“川普主义”(Trumpism),并指出其关注点已经从15世纪的“积累黄金白银”转移到了“国内生产”。他认为这种新重商主义浪潮并非“临时现象”,因为它背后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基础,市场不应将其视为可以自然消退的短期波动。巴切塞希尔大学教授拉赫米·因塞卡拉(Rahmi Incekara)则明确提出了“数字重商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21世纪的区块链生态系统和加密工具扮演着与黄金相似的“贵金属”角色,而技术所需的要素则可以在“数字重商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解读。
美国主导的数字平台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惊人的利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与负责任商业行为相关的巨大成本。例如,为保护数亿用户个人隐私而投入的巨额技术与合规开销、为有效审核和管理平台上泛滥的虚假信息、仇恨言论和极端内容所需的人力与算法资源,以及为避免利用市场主导地位进行反竞争行为而必须承受的商业模式限制。当欧盟以前所未有的决心,通过并实施《数字服务法》(DSA)和《数字市场法》(DMA)这一全球范围内最为全面和严格的数字监管框架,要求这些平台巨头必须为其平台上的内容负责、确保算法的透明度、并为用户数据提供更高水平的保护时,特朗普政府的反应并非将其视为一个主权地区为维护其公民利益和市场秩序而进行的合理立法尝试,而是迅速将其定性为一种精心策划的、旨在“蓄意伤害或歧视美国科技企业”的贸易攻击行为。这种反应逻辑,清晰地揭示了数字重商主义的本质,即任何试图将这些被外部化的成本重新“内部化”的努力,都被视为对美国核心经济利益和其全球技术领导地位的直接挑战。

图3 特朗普于2025年8月25日在Truth Social平台发布的一条帖文
2.2数字重商主义的四大支柱
特朗普政府围绕人工智能及数字经济所构建的政策体系,展现出高度的系统性和战略意图。参考王震宇、叶成城题为《特朗普政府的数字经济战略及其前景》的文章,其具体实践可以清晰地归纳为四个相互关联的政策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在科技领域实施“对内去监管,对外强遏制”的双轨策略。在国内层面,政府采取了去监管化方针,例如《消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地位的障碍行政令》和《美国AI行动计划》等。而在对外层面,则表现为一种毫不妥协的强硬遏制姿态。美国以宽泛化的“国家安全”为理由,加强了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扩散控制。核心是日趋严苛和泛化的出口管制制度,辅之以不断扩张的“实体清单”,并向拥有关键技术的盟友施加外交压力。所有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是系统性地抬高中国获取全球先进制造技术,特别是尖端芯片及其制造设备的门槛,从而延缓甚至阻断其在高科技领域的追赶步伐。

图 4 2025年9月4日特朗普在白宫国宴厅与美国科技界领袖共进晚餐(来源:Will Oliver/POOL)
第二个支柱体现为在金融领域,全力拥抱数字资产,以重塑金融格局并巩固美元的全球霸权。正如学者因塞卡拉所指出的,在数字重商主义的框架下,区块链和加密资产已成为21世纪的“数字贵金属”。通过签署《加强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等文件,政府不仅废除了拜登时代旨在规范数字资产市场的监管框架,更明确地将比特币等主流加密资产定位为美国推动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乃至维护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性支柱。同时,政府下令财政部等机构研究并建立一种由多种数字资产构成的“战略性储备”,其目的在于巩固美元的“强美元”地位,并寻求对新数字金融领域的战略控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战略对主权国家发行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表现出极端的敌视和排斥。
第三个支柱则聚焦于产业领域,通过实施“税收优惠与定向投资”相结合的产业政策组合拳,以保护国家冠军企业并吸引制造业回流。在减税的同时,政府通过一系列具有明确战略导向的投资计划,来引导社会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其优先发展的关键数字产业。这种做法旨在培育和保护一批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冠军企业”,并通过重塑全球供应链,降低对外部,特别是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高关税和国内生产为核心的“川普主义”模式,与历史上其他新重商主义实践者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前德国政府所推行的、被埃弗里称为新重商主义的模式,通过刻意压制国内需求、保持低补贴和低关税,最终实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策略。相比之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则更为直接和激进,试图通过极高的贸易壁垒来实现目标。
第四个支柱体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娴熟地运用关税施压与地缘政治胁迫的“双重威慑”策略。在特朗普政府的观念中,“美国优先”的核心要义在于最大化国内优势并最小化对外依赖。为此,其外交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交易性和进攻性。一方面,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关税作为其首选的经济武器,不仅针对战略竞争对手,也频繁地挥向包括欧盟在内的传统盟友。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更是为了通过制造经济痛苦来迫使其他国家在数字产业政策、市场准入和监管标准上对美国做出让步。
3.1战略三难困境
尽管特朗普政府的数字经济战略构建了一个横跨科技、金融、产业和外交四大领域的、看似雄心勃勃且内部协同的政策体系,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在其中占据资源控制、规则制定和技术创新金字塔顶端的单极化数字生态系统,但这一宏伟蓝图的实现路径上布满了内在矛盾。该战略最根本的困境,在于其试图同时满足三个本质上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这构成了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战略三难困境”(Strategic Trilemma)。这三个目标分别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这要求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国内产业的再工业化,这需要国家层面的强力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数字领域的单极霸权,这依赖于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一战略在执行过程中极有可能因为无法调和这些根本性矛盾,而最终退化为一种短视的“机会主义重商主义”,即为了迎合不同利益集团的短期诉求,而牺牲长期的国家竞争力和政策的连贯性与可预测性,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政策的内部矛盾和执行中的不确定性使得无论是美国本土企业还是国际贸易伙伴,都无法对未来的政策环境建立长期稳定的预期。此外,数字重商主义的零和逻辑带来了地缘政治风险的根本性提升。正如因塞卡拉教授所警示的,重商主义由于其内在的保护主义基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会“推动战争风险”(pushes risk of war)。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曾导致频繁的冲突和贸易战争,而现代数字时代的零和竞争,例如对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和数字贵金属的争夺,也正在重演这种风险。因此,这种单边主义的、以零和思维主导的数字重商主义,不仅在经济上制造了混乱,更在宏观层面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3.2超越零和思维
对于中国而言,特朗普的数字重商主义政策带来了复杂且双重的影响。一方面,美国通过强化出口管制,特别是针对先进半导体芯片和相关制造设备,试图在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上游“卡脖子”,以此来遏制中国AI产业的整体发展速度,这在短期内确实给中国相关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另一方面,这种极限施压的外部环境,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激发了中国内部加速实现技术自主创新的决心和紧迫感。
历史的经验反复昭示,重商主义政策虽然可能在短期内通过贸易保护和国家扶持,增强特定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但其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最终会因为抑制竞争、阻碍创新和毒化国际关系,而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桎梏。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尖锐指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体现了重商主义所有最坏的缺陷,却没有任何潜在的好处。在全球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时,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堡垒美国”模式,即通过军事化的贸易手段、地缘政治的胁迫,为少数特权群体的利益而强行占有和私有化全球自然资源,在实践上是不可持续的。
主理人丨刘典
编辑 | 车明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审核 | 梁正、鲁俊群